千古文明開涿鹿 2023-01-06 14:11
戲窩子的“角兒”
- 楊秀云 -
寒冷的冬日,暮色蒼茫中,走進涿鹿西頭堡村“晉劇博物館”,滿室五彩繽紛描龍繡鳳的戲服撲面迎來,全套樂器齊刷刷列陣,紙張泛黃的樂譜一本一本擺開……恍然間,響亮的鑼鼓聲熱熱鬧鬧響起,玫瑰紅大幕緩緩拉開,大戲開演了!

“最早的戲服是道光三年(1823年)的一件帔子,旦角穿的,紅色,樣式簡單,民間戲班傳承下來的……”霍漢清解釋,“年代越久遠的戲服越簡單。”霍漢清是涿鹿縣民俗文化協(xié)會副會長,山西梆子愛了幾十年。
“晉劇博物館”現(xiàn)有戲服兩百多件,其他戲曲文物一百多件。每件戲裝都裝著動人的故事。沒有了狂風(fēng)的阻隔,霍漢清的講解流暢快意。在他的描述中,那些華麗的寬袍大蟒仿佛吸附了一代又一代名角優(yōu)伶的魂魄,唰唰甩動長袖旋舞起來……

晉劇是民間的,不端架子,也不流俗,一招一式活潑潑演繹天地君臣,以百姓視角詮釋古今傳奇悲歡離合。不論何時何地,只要聽見晉劇山高水遠般的唱腔,我就會想起暗夜里看露天電影時風(fēng)中鼓蕩起伏的幕布,那是幾代人失落的舊時光,是飄散在故鄉(xiāng)上空的淡藍色裊裊炊煙,是從記憶深處泛起的綿密的鄉(xiāng)愁……聽了霍漢清的講解,我對晉劇的種種疑團找到了答案。

晉劇俗稱“山西梆子”,隨著桑干河的波浪流淌而來,始于明代固國安邦的大遷移。那些原本屬于長城的北方子民被連根拔起,像樹木一樣移栽京城,撐起被戰(zhàn)火毀滅的四梁八柱。他們凄惶的身后,連片的祖墳蒿草瘋長,鳥獸出沒間,隨風(fēng)傳來大漠戰(zhàn)馬的嘶嘶悲鳴。邊防重地,怎能千村薜荔?永樂十三年(1415年),朝廷重設(shè)保安州(今涿鹿所在地),撼動歷史的大移民起程,一批又一批晉國后人依依惜別世世代代生活的黃土高坡,扶老攜幼來到陌生的土地上筑屋耕耘。一步三回首,揪心扯肝的撕裂中,欣喜地看到滾滾東流的桑干河——從三晉大地流進懷涿盆地,像一根綿長柔韌的臍帶,把飄泊的游子與溫暖的母體緊緊連在一起,他們走了很遠很遠,沒走出祖屋前老槐樹下的母親河。跟隨他們前來的還有濃濃的鄉(xiāng)音和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(shù),“吃不膩的老陳醋,唱不敗的秧歌腔,改不了的鄉(xiāng)土音,嘮不完的老家常……”肩挑貨擔(dān)、車載貨物的晉商風(fēng)塵仆仆接踵而來,開商鋪,辦票號,行商變坐商,促進了經(jīng)濟文化的興盛。在晉商資助下,“山西梆子”落地生根,枝繁葉茂。史料記載,光緒年間,涿鹿縣五百二十三個村中有三百二十六座戲臺。到20世紀60年代,縣里還有一百八十六座。“姥姥門口唱大戲,搬閨女,請女婿,外孫女子也要去……”戲里融匯著老百姓的歡笑和淚水、愛憎和希望,不少老人站在戲臺下鑼鼓聲剛響便淚水漣漣……幾輩子的喜怒哀樂瞬間得到宣泄。“《二進宮》不算戲,拾狗糞的唱幾句。”一個劇種深深扎根于百姓心中,怎能不繁榮昌盛?

霍漢清在電話里邊說邊唱,嘩啦啦拉開年代久遠厚重華麗的大幕,一個又一個“名角”從歷史云煙中精彩亮相,他們的魅力在于藝術(shù)品質(zhì),也在于常人難以比肩的精神境界。20世紀60年代初,身為劇團團長的一代名凈蔡有山飾演《大名府》中的盧俊義,足蹬五寸高的厚底靴從兩張桌子摞起來又加一把椅子的高處跳下做“垛子叉”,不幸被腰帶里的鋼絲扎穿腸子,鮮血直噴,他跑到后臺草草包扎,強忍疼痛匆匆返回前臺,直到把戲演完才被火速送往北京,做手術(shù)的醫(yī)生說:“再晚到半小時,就沒命了!”“河北紅”席振德善于運用水袖、紗帽、搓手、頓足、搖頭、甩髯等藝術(shù)手法表現(xiàn)人物個性,飾演過一百二十二個栩栩如生的角色,七十八歲上臺依然震動全場。席振德任劇團負責(zé)人期間,從戲校學(xué)成歸來的女兒始終拿不上轉(zhuǎn)正指標(biāo),妻子也沒有安置工作。這位絕不“封妻蔭子”的“角兒”,長期無微不至照顧老師和師母,親生兒子一樣妥妥貼貼操辦后事為恩師送終。在歲月的風(fēng)雨中,他竭盡全力保護承載著幾代名角藝術(shù)之夢的戲裝,那些光華奪目的金絲線編織著黑蟒綠靠的華美,也編織著老藝人的精神高光。

六十七歲的霍漢清,聲情并茂地述說“山西梆子”的一枝一葉。我忽然覺得他就是一個“角兒”。他的老家溪源村與東窯溝同屬武家溝鎮(zhèn),位處商旅興盛的“古道”,曾為名角薈萃的“戲窩子”,祖上有自家“戲班”。他最早的記憶就是母親邊縫衣服邊拉著長聲哼唱《三娘教子》,“想當(dāng)年,留兒兩月半……小奴才,你看娘可憐不可憐……”唱著唱著,娘落淚,他也哭。童年在縣城度過,家門口就是戲園子,父親“票戲”,經(jīng)常攜著他的小手去看戲。霍漢清十一歲時曾有過輟學(xué)的經(jīng)歷。迷惘中,大灘里風(fēng)中翻卷著碧浪的葦子接住視線,他想起孫犁的《白洋淀》,“月亮升起來,院子里涼爽得很,干凈得很,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,正好編席……”他學(xué)得投入,很快掌握要領(lǐng),用別人三分之一的時間就編好一領(lǐng)席。他的聰慧引起老藝人的注意,“學(xué)戲吧!”“六爺”發(fā)話了,一言九鼎。“六爺”是遠近聞名的“六六旦”,曾和丁果仙、王桂蘭、劉玉嬋、郭蘭英等名家多年同臺,肚里裝了兩百多出戲,演誰像誰。六十六歲登臺吼出“一唱子”依然把臺下觀眾震得靈魂出竅。小漢清嗓子極好,“六爺”說他“有虎音”,能成“角兒”……春種秋收,時光流逝。大地解凍時,二十歲的霍漢清返城參加招工考試,結(jié)滿老繭的大手僵硬得好幾次把筆掉在地上,卻意外考了第一名。文藝因子浸潤骨髓,以另一種形式強身健體。之后,他自學(xué)拿到大專畢業(yè)證書。有了工作,有了學(xué)歷,唯獨放不下對晉劇的愛。可是,嗓子壞了,再也把不住調(diào)調(diào)。他改弦易轍,工作之余操起樂器,武文場件件信手拈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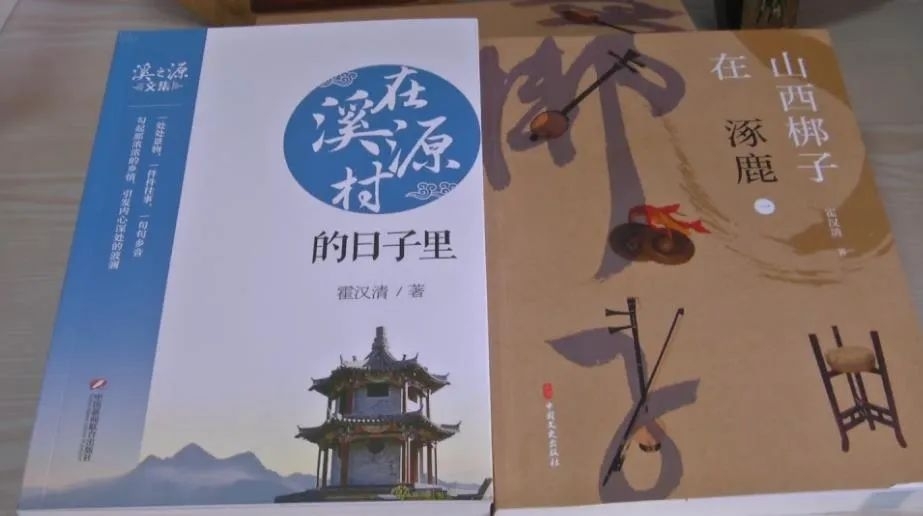
退休后,霍漢清投身于地方戲劇研究,所著七十萬字的《山西梆子在涿鹿》一書面世。義務(wù)為文化單位和觀光者提供服務(wù),同席振德、谷新聲等共同把幼年便陶醉其中的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》搬上舞臺,以晉劇表演紀念女作家丁玲……他說,縣里活躍著一批“文化人”,晉劇團輾轉(zhuǎn)城鄉(xiāng)唱大戲,“陶鄉(xiāng)”東窯溝就有老年晉劇團。
文化是一張彈弓,靠久遠綿柔的力量彈射!
高亢亮麗的“山西梆子”從簡陋的民間舞臺上傳來,攜帶著春夏秋冬時代云煙,化為桑干河上一波一波眩目的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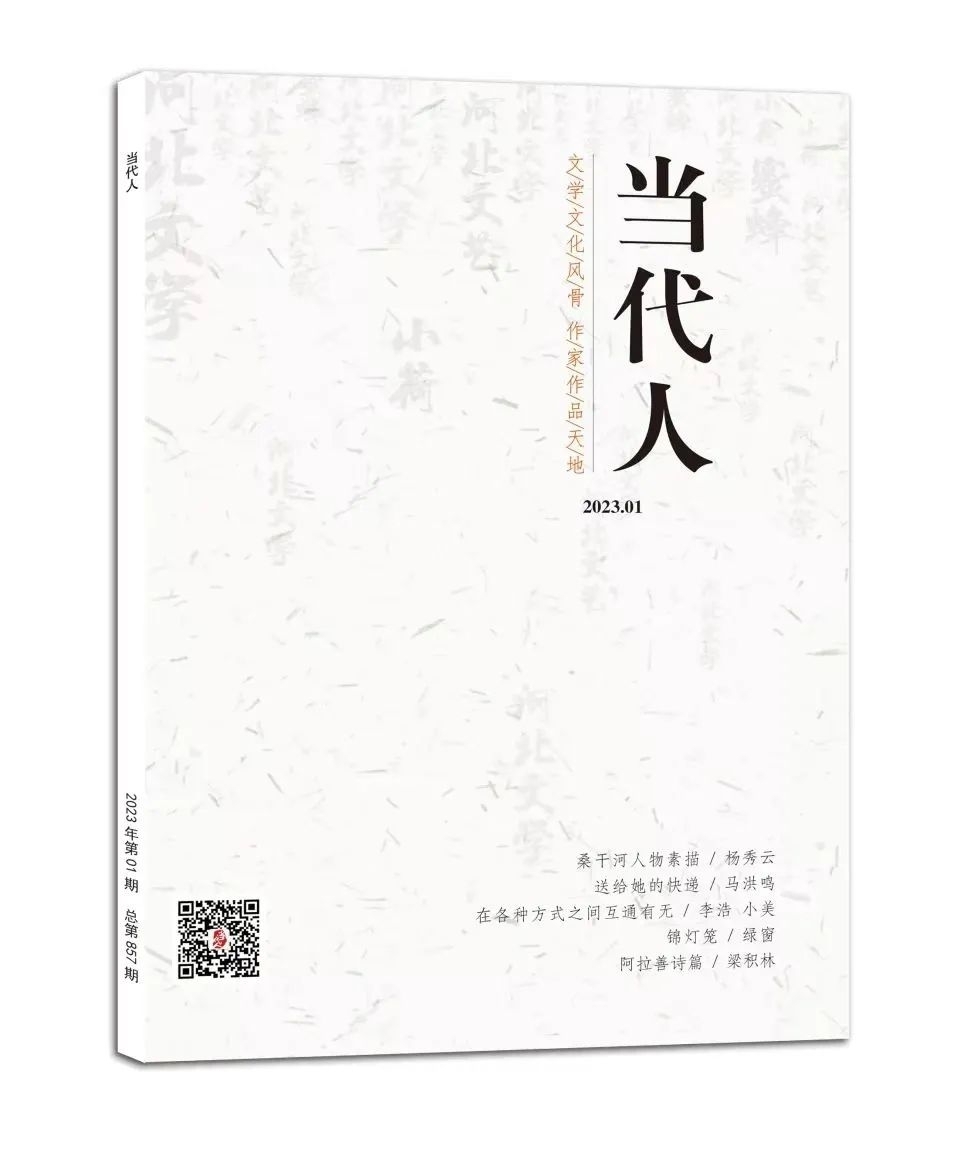
摘自《桑干河人物素描》

楊秀云,張家口市新聞工作者協(xié)會副主席。作家、文化學(xué)者。
[甘肅]白銀市景泰縣五佛鄉(xiāng):立足鄉(xiāng)土實際 推動黨的二十大精神落...
武鳴區(qū):跟進監(jiān)督 助力耕地“非糧化”“非農(nóng)化”治理落地生根

四川南充:明年起落地實施職工醫(yī)保“門診共濟”保障制度
外交部:今年又有5個國家同中國簽署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合作文件

【能力建設(shè)】湟源:以“四筑牢”為引領(lǐng),推動能力建設(shè)落地見效

寒潮來襲 黎平高速“一路多方”積極應(yīng)對保暢通
[青海]蘇青“握手”30個大項目成功落地

扛紅旗 當(dāng)先鋒 涿鹿鎮(zhèn):緊盯發(fā)展“第一要務(wù)”聚焦“抓黨建促鄉(xiāng)村...





